线上死亡与云哀悼:社交媒体该如何处理逝者资讯?_死者 Azim Pur城,孟加拉。图片来源:MD Mehedi Hasan/ZUMA/Alamy 我【指本文作者、心理学家Elaine Kasket,她的《机器里的幽灵们》(All the Ghosts in the Machine)一书于今年出版】提交文稿的时候很匆忙。我的主题是数字时代的死亡,而技术的变革日新月异。从我签合同到出版,这期间就释出了5款新的苹果手机。如果死亡是我唯一的关注点,就没有什么理由飞奔向出版社了。中世纪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1914-1984)认为,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西方对待死亡的态度只有少数几个重大转变。阿利埃斯的分类是从中世纪早期人们熟悉的、友善的、“驯服的死亡”到更晚近时期的更加可怕的“禁忌的死亡”,这时候死亡具有了“忌讳”的品质,我们很容易把它与今天联络起来。然而,有迹象表明,潮流正在转向。丹麦社会学家迈克尔·哈维德·雅各布森认为,自阿利埃斯时代以来,一种新的转变已经发生,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壮观死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生者与死者就像一包扑克牌,在互联网上不断地混在一起。如今,死亡的盛会在网络上演,吊诡的是,它让观众离得更近,也离得更远。 我没预料到,在悲伤和哀悼研究中会出现任何突然的、激进的发展,使我的研究成果变得过时。在对“网络哀悼和由科技主导的悲哀”的心理层面进行了十年的研究之后,似乎很明显的是,事物变化越多,它们就越是相同。数千年来,不同文化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将死者融入我们的生活,与他们保持某种形式的个人和集体关系。我们的超链接网络环境是专为纪念和延续与死者的联络而设计的——尤其是,线上下死亡时,死者的网络化身不会立刻消失。 不幸的是,在我这本书出版之前,死亡相关的法律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迟缓的法律体系在很多领域都难以跟上灵活的技术,在这方面也不例外。我们靠着一张相当过时的地图来导航,这张地图不太可能有什么帮助,但我们仍然要用它,因为它给了我们一种没有迷路的错觉。当我完成写作时,欧盟2018年通用资料保护条例(GDPR)刚刚出台,它将关于死者资料的决策责任简单地转移给了成员国。大型科技公司走进了法律匮乏和缺失造成的空白领域。 当然,科技公司可以像你换袜子那样频繁改动他们的条款和条件。在具有社会影响的科技巨头群体GAFA(GoogleGoogle、Amazon亚马逊、Facebook脸书、Apple苹果)中,至少Facebook已经在考虑这一问题和设计方案方面,做出了一些最为显著和持续的工作。早期,Facebook只是简单地删除死者的个人资料,这一政策随着该网站成为生活的纽带而改变,以至于它对死亡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到了2014年,Facebook的代表在管理的模式和说辞上,已经将公司定位成死者或明确或推测愿望下的看守人和保护者。“遗产联络人”系统于2015年上线,允许一名Facebook使用者指定一个资料执行人,执行人能做非常小的编辑改动,比如在使用者去世后新增好友。这就是我最后敲下“本书完”时的情况。 “遗产联络人”系统 出版的日子到了,我想一切终于结束了。但恰在此时,我在Facebook的联络人突然出现在“线上死亡调查网络”的群组里。他贴出了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刚刚释出的一项宣告——她透露公司正在推出一系列增强的纪念功能,并立即生效(意识到这些新政策可能会在我的书出版之前就让它过时,我的联络人为这种“强制性过时”向我道歉)。 我坐下来重看宣告中的细节。他们会让我的书变得多么不准确呢?有几件事确实发生了变化。据报道,每月有3000万人访问纪念资料,现在他们会在纪念页面上找到一个单独的“致哀”标签。遗产联络人变成了更大许可权的主持人,能够修改设定,编辑谁能写或读。人工智能现在能用来遮蔽死者的生日提醒,以及在下一场活动中邀请死者的建议。那时,我没有感到恐慌,而是意识到我的中心论点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 我们可能会赞赏Facebook愿意处理网站上已故者的资料问题,特别是在只有很少的公司关注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然而,无论Facebook和其他任何大型科技公司推出怎样的系统和规则,人类对悲伤的癖好还是会让他们一次次地不知所措。当人工智能判定一个Facebook使用者已经死亡(在社交媒体上死亡)时,对每一个被暂停的生日提醒,有的哀悼者会松一口气,但也有人会再次体验到失去亲人的伤痛。当一位我采访过的母亲停止收取已故女儿的生日提醒时,她变得非常难过。这位失去至亲的女性说,“对我来说她还存在着。她还在Facebook上,今天仍然是她的生日。”即使是出于最善意的努力,去找到造成痛苦的缘由和不造成痛苦的办法,Facebook的工作人员还是掉进了一个常见的陷阱:错误地认为悲伤比实际上更容易预测、更单一。如果悲伤一直持续,对商业固然更好。但是个人和集体的丧亲之痛的实际复杂性给任何网站都带来了设计难题,当然,这些网站最初的使命宣言不包括变成一个线上墓地和哀悼者联络服务,并且也没有把这一功能算入预算。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社交网络公司是连线活着的个人,向用户卖东西,把使用者的资料商品化的盈利机器。它们不是慈善机构、公共卫生组织、非盈利墓地或职业悲伤顾问。活着的时候,我们把大量的个人资料交到它们手里,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最初注册登入时,也任命它们在我们死后按照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我们的资料,而它们似乎缺乏合适的资质来承担这一角色。蒂姆·伯纳斯·李爵士(注:万维网的发明者)对于他的作品发展出来的局面感到震惊,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对万维网去中心化,重获对个人资料的控制权。事实上,在我们死后,大型科技公司对这些资讯的所有权——其中可能包含我们最珍贵的记忆——仍有增无减,这似乎是赞同他的最有力的理由。 最近,Facebook通过赋予“遗产联络人”更大的权力,用自治来强化其家长式作风。这减轻了他们自己处理特殊请求的负担,这可能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们有很多死者和无数哀悼者要考虑。如果Facebook的财运持续下去,他们会发现,到了本世纪末,他们将拥有近50亿个死者档案:将更多管理纪念资料的责任交到真正了解死者的人手里,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照看一份数字纪念资料可能是一项艰钜的任务。一位我采访的悲痛女性,在一连串令人心碎的亲人离世之后,发现自己是Facebook上多个纪念页面的管理员——女儿的、丈夫的、女婿的,以及她最好的朋友的。失去亲人多年之后,她仍然对哀悼者群体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她来说,节日和逝世纪念日变得如此沉重,以至于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她从社交网络上下线稍作休息——这无疑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举动,但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时代,也会引发深深的负罪感。 我已经成了科技作家痛骂的物件,古板过时,或者至少是被批评的一员。让我显得更加愚蠢的是,我选择了一种传统的、僵化的载体来描写这样一种即时的、多变的现象。幸运的是,基本的资讯没有改变:决定如何管理和访问你放在网上的个人资讯的权利,以及在你离开后由谁来继承的权利,都是可以争取的。 (翻译:鲜林) 获取更多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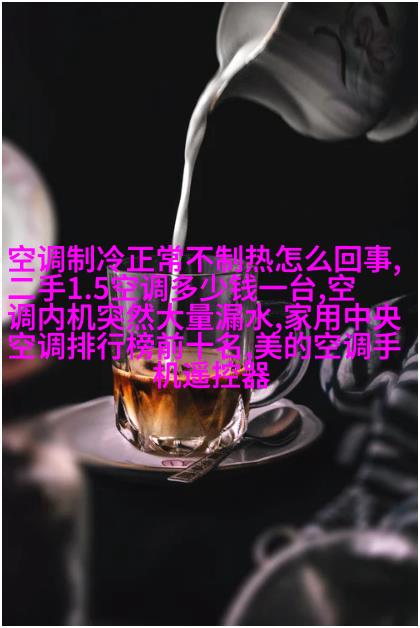

梓辉家电信息资讯网
线上死亡与云哀悼:社交媒体该如何处理逝者资讯?_死者 Azim Pur城,孟加拉。图片来源:MD Mehedi Hasan/ZUMA/Alamy 我【指本文作者、心理学家Elaine Kasket,她的《机器里的幽灵们》(All the Ghosts in the Machine)一书于今年出版】提交文稿的时候很匆忙。我的主题是数字时代的死亡,而技术的变革日新月异。从我签合同到出版


